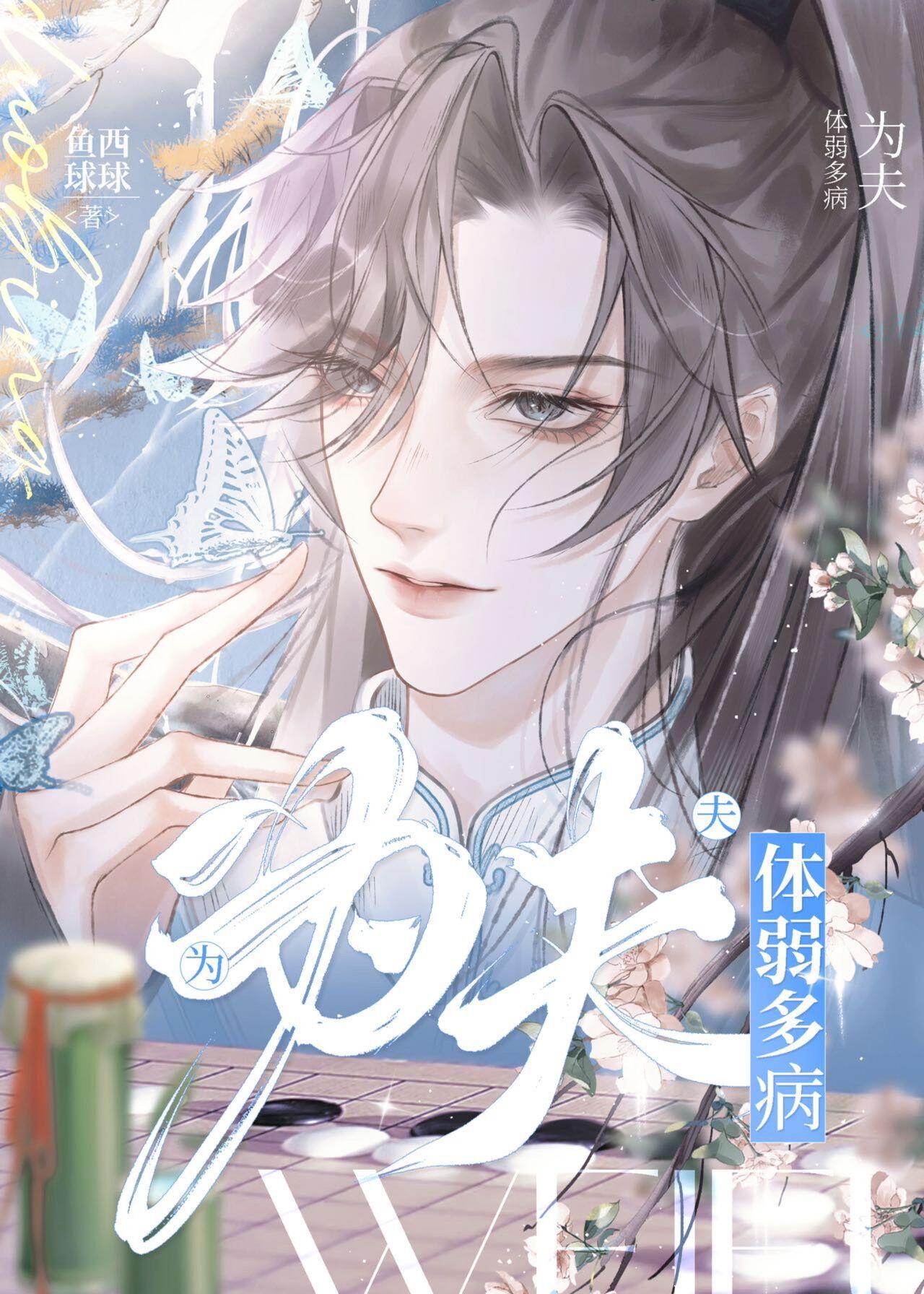屈服小说网>忽悠华娱三十年 > 第七百一十三章 恋爱脑那扎天才枪手逆势爆发(第3页)
第七百一十三章 恋爱脑那扎天才枪手逆势爆发(第3页)
宁皓驻足片刻,嘴角微扬。
他知道,这不是官方文件,也不会被教育局承认。但它会存在,就像那些自发传唱的童谣、莫名浮现的影像、无法删除的空白推送一样。它不属于任何系统,却深植于人心。
他继续往前走,穿过清晨的街道。路过一家便利店时,店员正往橱窗里摆货。那是一排新上市的儿童饮料,包装设计极简,主色调是深蓝,瓶身上印着一行小字:
>“每一口,都藏着一个没说完的故事。”
宁皓买了一瓶,拧开喝了一口。味道很普通,甜中带酸。但他分明感觉到,一股暖流顺着喉咙滑下,直抵心脏。
他掏出手机,打开录音功能,对着空气说了句话:
“我是宁皓。我没有死,也没有逃。我只是完成了我的部分。现在,我把话筒交出去。谁想接着讲,就请开口。不用怕讲错,因为这个故事本来就没有标准答案。”
录完后,他点击上传,平台显示“发送失败”。他并不意外。
他删掉录音,把手机放回口袋。
走到路口时,一个小学生模样的男孩骑车经过,忽然刹车,回头看他:“叔叔,你是不是讲过‘云上影院’的故事?”
宁皓怔了一下:“你怎么知道?”
男孩咧嘴一笑:“我妈说的。她小时候听过一次,记了一辈子。”说完蹬车而去,背影很快消失在晨光中。
宁皓站在原地,忽然觉得全身轻松。
他知道,自己已经不需要再做什么了。
故事已经脱离作者,进入了野生状态。它不再依赖某一个人的记忆或设备,而是在语言、歌声、眼神、手势中不断再生。每一次讲述都是一次重写,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参与。它不再是电影,也不是小说,而是一种新型的社会基因??通过叙述传递信念,通过共情构建现实。
几天后,乌镇的老屋被人发现空无一人。木牌“修笔匠”仍挂在门前,但门锁已锈死,推门进去只见桌上留着一本册子,封面空白,内页密密麻麻写满了字,全是孩子们口述的梦境整理稿。最后一页写着:
>“我不再是讲述者,我只是第一个听见的人。
>如果你读到这里,请继续写下去。
>下一个梦,由你开始。”
册子很快被人拍照上传,虽屡遭删除,却总在新的平台冒头。有人称之为《梦典》,开始自发翻译、注释、续写。两年后,某大学开设“民间叙述学”选修课,教材之一便是这本匿名手稿。
而宁皓本人,再未现身。
有人说他在西北某村教书,教孩子们用沙盘讲故事;有人说他隐居雪山,每日记录风声里的歌词;还有人说他根本没离开过南京路小学,只是变成了那面蓝旗的一部分,随风飘荡。
但更多人相信另一种说法:他化作了某种频率,游荡在每一个愿意开口讲述的瞬间里。当你鼓起勇气说出“从前有个梦”,你就接通了他。
2025年春天,全国中小学语文课本修订,新增一篇名为《蓝裙子姐姐》的课文,讲述一个女孩如何用故事点亮黑暗。教材编写组称其为“寓言”,但插图中那位主角的裙摆颜色,恰好是RGB值#0D3B66??一种极为罕见的深蓝,曾出现在三十年前一部被焚毁动画的色卡档案中。
同年夏天,一位盲童在朗诵比赛中夺冠。他朗诵的是一首原创诗,题为《我看见的电影院》。评委问他:“你从未看过电影,为何写得如此真切?”
他回答:“因为我听过很多人讲。讲得多了,心就看见了。”
台下掌声雷动。
而在观众席最角落,一个戴帽老人默默起身离去。没人注意到他袖口露出的一截炭笔,正散发着淡淡荧光。
多年以后,当新一代孩子问起“Y9是谁”,长辈们往往会笑着说:“那是很久以前,一群不信‘不可能’的大人和孩子,一起编出来的一个梦。”
至于梦是否真实?
他们会指着窗外说:“你看,今晚的星星特别亮,是不是像放映机打出的光点?”
而每当有人在深夜轻声说起“蓝裙子姐姐”,远处总会传来一阵若有若无的合唱,歌词始终如一:
>“如果你愿意相信,就能看见门;
>如果你开始讲述,门就会为你打开。”